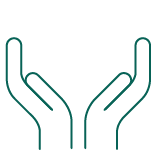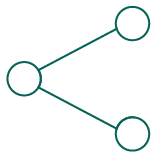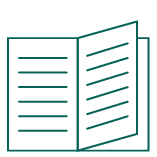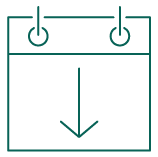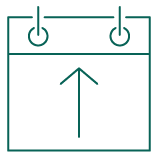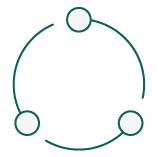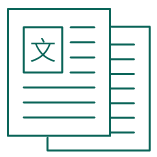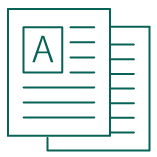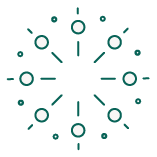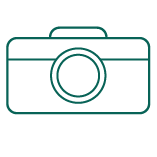專訪 H.P.Blavatsky
在1991年初的頭幾個星期,我來到了倫敦,準備與英國和愛爾蘭新衛城(New Acropolis)的主要負責人進行定期會議,他們也是跟我有一樣的目的來到這裡。
在某個典型英國寒冷多雨的早晨,我造訪了一個我經常去的地方 - 波多貝羅市場,裡頭有成千上萬的骨董、古玩和手工藝品。我記得我們離海倫娜.彼得羅夫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 (H.P.B.))最後居住的房子不太遠,她大部份的不朽著作《The Secret Doctrine (奧祕的信條)》都是在那裡完成的。計程車將我們放在蘭斯唐恩路17號的門口,讀者們可以在文章中看到在那兒拍攝的照片。
那一帶雖然與過去相比繁華了不少,但在一月寒冷的細雨下仍讓人感到清幽與宜居。而正是這樣的氛圍讓我有了撰寫這篇文章的想法。這正是一個穿越時空回到一個世紀前的好機會,去拜訪當時居住在這棟房子裡的偉人。
所以,接下來的部分為虛構…但也或許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其實我自己也不太確定,畢竟就像我在生活中所理解到的,事實與虛構之間並不總是如我們所想的那麼分離。
在畢達哥拉斯學校中,針對求學者(又稱為 akousmatikoi)的其中一項入門測驗,是讓他們看在白紙上的三個黑點並請他們回答看到了什麼,只有當求學者回答出”三個黑點”時才算通過測驗,其餘回答三角形的人則會被取消資格。藉由運用想像力 - 更多時候是幻想 - 將事物連結在一起並不是一種美德。真理是更為美麗、更為簡單的。但當它被過度解釋的時候,反而會不容易被理解。關於這部份我想保留空間給讀者們,去相信任何你們想要或能夠相信的東西吧。
***
馬車將我送到了同一個門口 - 蘭斯唐恩路17號,這天的天氣很好,陽光 - 在倫敦相當罕見 - 在所有事物上都閃耀著燦爛的光芒。
我知道布拉瓦茨基夫人知道我會來,我發現自己有點早到了,於是花了點時間慢慢走在通往大門的小徑上,抵達後我拉起門上的黃銅把手扣了扣門。這扇門與整棟門面看起來似乎是新粉刷過的。
一位女士(可能是僕人)請我進入一個小廳。我將我的拜訪卡遞給她,在她從另一扇側門消失前她告訴我,我可以進去了,布拉瓦茨基夫人正等著我。她就在那兒:宛如神秘般的H.P.B.坐在一張寬敞的工作椅上面對著辦公桌,桌子前方是一扇大而明亮的窗戶。她的兩旁擺著幾張桌子,上面有一些鬆散的手稿與成堆的打字紙。
她看起來與照片上的她很像,不過更多了點人的感覺,更和善與親切。她的穿著十分簡樸,肩上披著幾條深色的披肩,邊上帶有流蘇,其中有些是彩色的。她面帶著笑容伸出她的手,那手很豐滿,手指非常柔軟纖細。我向她打招呼、互相致意,並解釋為什麼我會來到這裡。她的眼睛大且突出,令人不安的灰色雙瞳帶著好奇而又調皮的神情看著我,我想雖然我已經很努力隱藏了,但我緊張的情緒還是逗樂了她。
她拿起一支又粗又舊的藍色鉛筆,對我做了個手勢,問我是否願意在房間裡等一會兒,因為她正準備為她在撰寫的書中的一句話做收尾,那本書名叫《The Secret Doctrine (奧祕的信條)》,而它的涵蓋範圍將會比《Isis Unveiled (伊西斯揭秘)》來得更廣泛。
這房間相當大 - 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風格 - 我注意到H.P.B周圍有許多小桌子和書櫃。她似乎患有嚴重的水腫,讓曾經靈敏的身體變得異常粗壯,使她幾乎無法從椅子上站起來。我從後方看著她,她被透過窗戶灑進來的光線包圍著,從窗戶望去可以看到那佈滿荷蘭公園的翠綠。

我盡可能安靜地在房間裡穿梭走動,房間後方雜亂無章地收藏了成堆的書藉、羊皮紙、布卷 - 裡頭大概寫有文字,來自印度其象徵意義遠大於它們是骨董或擁有精細做工的青銅器,阿多尼的掛毯、莫拉達巴德的木制盤子、克什米爾的瓷磚、僧伽羅的圖像,而地板本身則被帕爾加特的編織地毯覆蓋著。還有一些我認不出來的奇怪小雕像、岩石、小化石,讓整個房間充滿了一種異國情調。這些收藏是在前往遙遠國度的旅途中獲得的,對一般遊客而言沒什麼價值,整個感覺就像是某個充滿冒險精神的老勳爵的書房,而不是一位俄羅斯貴族夫人。
我沒有注意到H.P.B.的椅子是旋轉式,而她已經不再背對著我了,一邊以一種有趣的表情看著我,一邊等我結束我的巡禮。我說了些理由解釋我的行為,並向她走近,坐在她示意的一把距離她約6英尺的木椅上,旁邊是一張桌子,上面有幾張紙。
她仍面帶微笑看著我,並遞給我一根手捲香菸,我婉謝了她。她為自己捲了一根菸後用長火柴點燃。一小片煙霧彌漫開來,這股氣味讓我想起了我熟悉的土耳其香菸。
此時一位身穿灰色與黑色衣服的女性身影從右邊出現。她非常恭敬地走近我們,俯身在H.P.B耳邊低聲說話。
『伯爵夫人想知道你是否想喝點茶。』她直接地說。
聽到這句話後,我頓時覺得尷尬迅速站起身來,因為我以為這個人只是一名女僕。我接受了這項提議,但在我還沒來得及說些禮貌的話之前,她便輕輕地、親切地鞠了個身後,便消失在另一個房間裡了。
我再次感受到H.P.B.那被逗樂的神情,因為她問:
『你是不是以為剛剛進來的女士是個精靈?』
任何來自於這個問題的嚴厲都因她的微笑而消失了。但她灰色有如薄霧的雙眼,以及那通透的瞳孔,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我忍不住盯著一支銀鈴,想起了據說在H.P.B.出現時會發生奇怪現象的傳聞,其中有許多令人稱奇的事,包括了發出聲響的搖鈴。她注意到我的視線,一如既往感到逗趣的向我解釋,這是當她需要康斯坦斯伯爵夫人時傳喚她用的。她補充說,這位尊貴的女士不僅是她的好朋友,也是一個傑出的徒弟。現在的她有能力與高等生命有所連結,只要她不那麼忙於時時照顧她的時候。
「夫人…請原諒我的失態。我來是為了要專訪您的,但我現在不曉得該從何開始。因為當我知道這裡有《The Secret Doctrine (奧祕的信條)》的原始手稿後,我所有的問題就都消失了。」
『好,那先喝口茶讓自己冷靜一下吧…我也喝點咖啡。』
她指向我剛剛手肘靠著的桌子說道,這時我才發現桌上多了一個胡桃托盤,上面擺了一整套完整的銀制茶具,看起來應該蠻沉重的,雖然我沒有注意到是誰把它放在那裡,甚至是查覺到有人進來過這個房間。H.P.B喝著咖啡不再面帶微笑,而我不想表現的過分好奇,於是我也喝了我的茶,非常燙也非常香的錫蘭茶。
「看到剛才康斯坦斯伯爵夫人如此謙虛地站在這裡,讓我想起常有許多貴族與夫人、將軍和學者環繞在您身邊與您接觸,感覺社會上層的人們都深受您的吸引,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您為許多出身卑微的人,特別是印度教徒提供了友誼與幫助。您能多告訴我一些有關這方面的事情嗎?」
『我讀過你寫的一些東西,的確,這幾個世紀以來真正發展的並不是人類本身,而是人們的科技、工具和彼此聯絡的方式。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19世紀的話,有些事我想先讓你多了解一下。
我是1831年出生在俄羅斯的一個省級城市,差不多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在我生活的時期裡有一些是你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部份;當時即便是在中歐,也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目不識丁,只有非常少部份的人上過大學。除了少數的特例外,成為一個高尚的貴族並受到良好教育,是當時證明你擁有社會與經濟地位的主流象徵,特別是對於男人而言。因為我們女人被賦予的期待是只要會說法語、會演奏樂器,並能優雅地應對一些相當複雜的社交禮儀就足夠了。頂多再多幾次出國旅行的經驗,或是對於藝術畫作有些自己的想法。
此外,書藉都是少量出版,而且在大部份情況下它們的裝訂成本都很高昂,這使得靠薪水生活的一般人很難可以接觸到。由於很少有女性可以上大學,她們大部份都得待在家裡自學,而公共圖畫館的匱乏,讓在自己的城堡中擁有一個私人圖書館是件普遍的事,像是我的祖母,而這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相信我,人類在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即便到了20世紀也會持續朝這個方向前進,至少在歐洲、北美和你所居住的世界的主要城市皆會如此。假如今天有誰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那只會是因為他們不想要…但不會永遠如此。』
「儘管是這樣,但您還是讚揚許多印度教徒的智慧,甚至是知識。」
『是的…雖然在19世紀中期的印度情況有些不同,但就本質上來說是一樣的。在種姓制度下,只有”婆羅門”和部份的”剎帝利”可以接觸到更高的文化。我在書中提及的聖賢都是有資格進入令人嘆為觀止的圖書館,或是接觸到傳統典藉的老和尚們。像我的導師們都是王子,因為在那裡,一個人的種族身份所代表的不光是他們的祖先,也與他們的精神發展息息相關。比如說,假如你今天遇到一個會讀梵文的搬運工人,你可以確定他是一名徒弟,正在進行試煉的"lanoo",而且非常有可能一直到最近,他都是住在宮殿裡。
還有,在我年輕的時候,從美國傳到俄羅斯的奴隸制是一個事實,但我指的並不是像奧古斯都規定的那種。這些人是為了生存而生活著的,他們不會去管什麼快樂還是不快樂,事實上他們沒有時間或興趣去著重在科學,不論是開放的還是深奧的,對他們來說,只有信仰、迷信、和傳統療法等等。』
「但當您還是小孩的時候就開始與這些天真且單純的人們有所接觸,甚至是去認同他們的信仰。我這樣說對嗎?」
『不完全是…不過因為受到"宗教"恐懼的強烈影響,使他們產生不可被撼動的教條以及對信仰的狂熱的部份,是我學習的動力也給了我研究神秘學的方向。』
「夫人,大家都知道您是H.P.B.我不想八卦,但我的讀者經常問為什麼您叫"布拉瓦斯基"?這是您丈夫的姓氏,而他是一位年紀足以當您祖父,而您也拒絕與之共同生活的人。我知道這不是出於經濟考量,因為當您取得美國公民身份時,您自動放棄了作為一名俄羅斯將軍遺孀所能獲得的巨額養老金。相信也不是出於社會地位考量,因為您是貴族出身,而且與沙皇家族有親戚關係。所以,為什麼是"布拉瓦斯基"呢?」
『其實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並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多重要。我之所以早婚只是為了要擺脫家裡的控制,為了要強調這點,我冠上了我丈夫的姓氏,而這在當時也是很普遍的習俗。後來我也習慣了這個名字,以及這樣的姓名縮寫,如果我用回了娘家姓,對我來說感覺反而是一種對這位老先生的不尊重。』
「我們換另一個話題,您攻擊了關於通靈這件事,還不斷教導大眾這對靈媒的"星空體 (Astral Shells)"會造成多大的折磨。但為什麼您在明知道這會為您帶來什麼樣問題下,卻還是練習通靈呢?而且,在某些場合裡您不就是所謂的媒介嗎?」
『通靈在19世紀中期是一種爆炸性的現象。但這在不同時期的歷史上都曾經發生過,甚至在《舊約聖經》中還載明了做這件事情的人會受到遣責。然而召喚死者的魂魄,或那些試圖偽裝自己是死者的鬼魂,一直以來都是取代正統"宗教"最流行也是最簡單的方式。因為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的興起,導致了包括亞洲在內所有已知宗教的衰敗,有一些教派,像是基督教的教庭與神職人員,其敗壞程度糟到令人難以致信的地步,這也因此讓”白色階層 (Hierarchy)”決定要助長通靈的發展,好為人們的靈魂提供暫時的養份。
我並不是要攻擊通靈,我只是指出它是什麼,以及更重要的是它淪陷在什麼樣的現象當中,而這現象通常是在宗教本身的推波助瀾下發生的。我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媒介",就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在童年和青少年的時候就是一個媒介了,而我的導師始終伴隨在我身邊,他強大的僕人也保護著我。』
『大概在我二十歲那年,某天我與父親在海德公園散步的時候,我親眼見到了我的導師,就跟我過去多次在”星光 (Astral Light)”中見到的他一模一樣。一直以來我都"覺得"他還活著,是一個真實具有實體的存在,但當我發現他是真的活著的這個事實時,還是給了我一個非常強烈的震撼。那天在公園遇見他,他正被其它印度教政要包圍著,正當我準備要走近他時,他注意到了並意示了我不要過去。我把這一切告訴了我父親,因為那時他非常支持我。第二天我獨自回到同一個地方,而我的導師已經在那裡等我。我們一起在公園裡散步了幾個小時,還聊了很多事情。』
『當然我沒有辦法鉅細靡遺的跟你說我們聊了哪些,但主要內容都是與我有關的。他向我解釋了為什麼我會如此與人不同,也跟我說了所有這些的原因。他還提到了我在這一世必須要去做的事,尤其是關於我要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以及那些顯現在我面前的元素精靈、看不見的生命和奇異的能量。他還給了我關於旅行、人們、書藉的建議…我想這話題就先到這裡吧?』
「您指的是K.H.導師嗎?」
『不好意思…不過你會在你的文章中提到導師的名字嗎?因為現在訊息已經流露到了外界而導致諸多誤解,以及爆發了仇恨與不諒解的風暴。在我們渴望傳播這種我們稱之為神智學的古老哲學的過程中,我們獲得了許多朋友,在對抗蒙蔽真理的黑暗中也掀起了有所助益的騷動。但我們也同時向公眾開放了一些本應受到尊重卻被人們輕蔑的神聖書藉,好在幸運的是,這些書只是以零散的形式出版,而且內容有做過許多改動。 對我而言,那是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一部份原因是因為面對太多的不正義而使我無法控制自己的心性,以至於我現在病得很重,幾乎感覺不太到這孱弱的下半身。』
「夫人…聽到這裡我不禁想請教,明明妳在專注與心智的發展上,都有著非凡的精神力與卓越的能力,為何還會如此容易受到那些人們因本性和信念,而註定會採取那些顯而易見的攻擊呢?」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自己也不完全知道答案。但如果要做個比喻的話,可以試著想像一個在化學實驗室中的試管,在這個試管內的實驗反應會釋放出強大的熱能與不同型態的震動。但一個容器能夠承受的壓力有限,所以當裂痕與燒焦開始逐漸出現時,容器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自毀,甚至可能會波及到最接近它的人。不過任務必須完成… 而試煉不是重點。因為它最終會毀滅,之後便會回歸塵土…我希望我的遺體被火化,我的骨灰被揚灑。而這試管只是 - 在你們20世紀會怎麼形容? - 被汙染了。』
「請多告訴我們一些關於神智學校 (Theosophical Society)的事情吧。」
『你應該比我更瞭解它的發展。但我不能、也不想知道任何關於它未來的細節,但我可以跟你說說它的過去,在我年輕時第一次去到埃及,想在當地建立一個研究神秘事物的組織或中心。接著,多年過去了,後來我在紐約遇見美好的老奧爾科特,我們在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朋友以及一些懷有單純好奇心的人的幫助下,試圖在紐約也做同樣的事。之後在我導師的允許下,我們於1875年11月17日正式成立了神智學校。在草創初期我們雖俱備熱情卻不曉得該如何進行,所以它的原則在形式上更改了好幾次。
不過,在導師的建議下,最後我正式擔任的角色只是一名通訊秘書,因為我在未來將會進行很多趟旅行。真正的創始人是奧爾科特上校,正如你所知的,他是一名律師,也是一位通靈與唯靈論的專家。』
『我知道會有這麼多人對神智學校有興趣,主要是因為我的緣故。如今學校有三個主要的影響中心,分別是在美國、英國以及位於印度的阿德爾城市,也許未來有天阿德爾的學校會成為正式的總部,不過目前而言,它只是名義上的總部,而非正式的。
我知道,我為學校帶來了很大的傷害,因為我的關係,讓學校遭受許多宗教與科學狂熱份子的攻擊,使它的名字和許多學員的名字都被汙名化了。但我從來沒有欺騙過任何人,我也不需要這麼做。因為在我的情況下,那些所謂超自然現象的產生,對我來說只是很理所當然的日常,反而是要如何刻意不讓它們發生才是真正困難的事。但,我沒有足夠的技巧去知道該如何控制它們,好讓我能避免那些被嫉妒影響的靈媒,或那些意識能力不足渴望獲得關注的人找上門。
現在我在進行《The Theosophist (秘密教義)》修稿的同時,我也在為校內期刊《神智主義者》以及其它神智學和科學的期刊撰寫文章,逐漸形成了一些人所謂的布拉瓦茨基專欄:這是學校真正的核心部份,真正的奧秘學校。
我知道有很多人還沒有準備好,但這就是所有我能做到的事;與現有的一切可能資源合作。若不這樣做的話只會更糟,儘管有時候我仍會有所懷疑,曾經引導我多次的內心之聲已不再響起,我的星光鏡(Astral Mirror)也不再反射任何事物。但我依然服從並竭盡所能地去執行我被賦予的任務。』
『另外我也有在考慮編一個《The Theosophist (秘密教義)》的術語一覽表。裡面將會包涵許多關於教學目的的圖表,而它們也會隨著時間推進而增加。』
「對於我們這些欣賞您非凡且承接超乎常人的任務的人來說,我們特別感到沮喪的是,您的一些時間被那些好奇的人們給佔用了,他們可能是要您展示現象,或與您私下進行諮詢。我知道導師們為了讓您完成您的任務而不得不給您…一些額外的能量。但為什麼您要把這些能量浪費在那些沒有實際意義的現象上呢?」
『請原諒我,但每個人都有權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或盡其所能地去過自己的生活。所謂的自由,並不是羊群可以投票給牧羊人就叫作自由,而是更深遠的東西。自由的本質是完全個人的,且無法被轉讓的。』
「抱歉…我並不是要指責您的態度,只是在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對您如此的忘恩負義,以至於您在某種程度上,只能倚靠朋友和徒弟對您的個人情感來去推行世界運動,而不是立基於他們也有共同的信念。」
『這是一種與你不同的工作方式,但這是我的工作方式。無論權威是以怎樣的形式呈現,只要它沒有牢固地建立在精神大同的基礎上的話,那麼在我看來都是荒謬。這可能是我的眾多缺點之一,不過這也是身而為人皆無可避免會遇到的個性的挑戰。每個人都一樣,不過話說回來,如果生活中少了這種真實性的話,又會是怎樣呢?
的確,有時候我會抱怨生活,但我喜歡和那些與我想法不同的人,在漫漫長夜中一起去討論那一千零一個話題;當他們向我提出要求時,我很難拒絕他們。我並不認為超自然現象有什麼好重要的,但它們自古以來就已經存在且被使用了。比如說,如果你把那些現象從聖經中拿掉的話,那麼《舊約》只不過是部記載了一個部落經歷了什麼考驗與磨難的故事,而《新約》則是一本列出種種道德訓誡的清冊,就好比斯多葛學派(Stoics)的著作一樣。
超自然現象是一個無法被完全忽略的成分。如果它們是被真誠且不帶任何利益動機運用的話 -- 儘管如此還是非常危險 -- 那麼人們會將一切所見所聞深深烙印在心,這比任何口頭或文字上的教誨都要來得管用,尤其是對於那些害怕生死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所有人都害怕生死循環中的某些方面。光是記住前世是不夠的…相信你自己也很明白。』
「當我們的意識處於神之地(Devachan)或天堂,或任何不管我們如何稱呼它的地方時,為什麼我們會不記得在那轉世過程中的一切呢?」
『因為人們試圖要記住的是他們屬於凡人的部分,但如果是這部分的話,那我們就只能記住我們作為凡人的存在。但假使我們將意識提升到永恆不滅的那部份的話,那我們就可以獲得如柏拉圖和許多啟蒙者所說的,那些關於天之生命的訊息了…現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需要回到我的工作上了。因為它的進度很慢…有時候我需要花上兩天的時間,才能從那些我永遠都沒有時間去閱讀的資訊、格言或最近出版的書藉中有所收穫。
謝謝你決定進行這次的採訪,以及讓你的學生們知道我的作品不是他們的天花板,而是一扇門。無論如何,未來看起來總是艱難,花太多心力去思考往往只會令人感到沮喪。倒不如就直接開始去做我們要做的事,而不是花時間去制定一個長遠計畫。』
「夫人,謝謝您的存在。您就像您所說的那條將許多智慧之花繫起來的繩子那般,讓我們在越來越多虛話中懂得一些真實而有意義的事。也謝謝您的茶,出現的如此神秘…」
『也許多年之後,這場採訪唯一會被人記得的是這茶的”出場方式”。』
H.P.B.笑了起來,心情似乎很好,儘管我感覺到她有些疲倦,但她的雙手已經機械地回到她的稿紙上。我起身向她道別,感覺這一切好像只過去了幾分鐘。
新訪客被帶到了門口,因為這天是星期六,看來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訪客一如既往地絡繹不絕,即使他們已經是被挑選後的少數人。我不禁對自己微笑,心想,H.P.B.永遠不會改變。她是一個現象;她知道,且無意隱藏。
夕陽逐漸西下,我慢慢地走進黑暗之中,懷裡緊揣著我的筆記本,彷彿它是一個寶藏,而我必須要牢牢記住它以完成這場專訪。